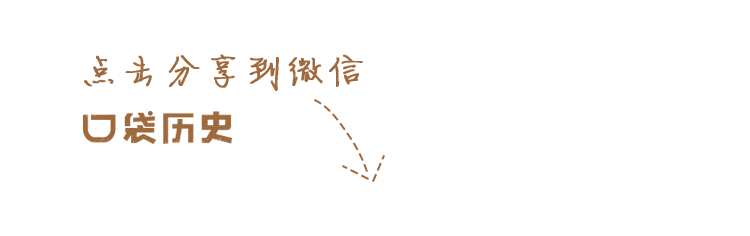雀金裘与红楼流行服饰
现在特别流行的就是将中国元素融合到时下的时装中去,什么龙袍穿上身,裹着大花袄子,美其名曰“中国元素”。其实这是一种对中国元素的误解,诚然,青花瓷,描龙绣凤是中国风的一种,旗袍汉服也是中国特色。但是这只是中国风的冰山一角,并不是全部,仅《红楼梦》一书中的中国美服就远远高于时下的所谓中国元素。其服饰中的用料,一是品种多,二是高档、名贵,有些可说是稀世之宝。书中出现的服饰用料,主要有"大红洋缎"、"撒花洋绉"、"起花八团倭缎"、"秋板貂皮"、"灰鼠皮"、"黄绫"、"羽缎"、"白狐腋"、"
而它的做工包括原料做工要求非常高的技艺和缝制技艺。例如书中写到:"缕金百蝶"、"五彩刻丝"、"插牙背心"、"二色金百蝶穿花"、"五彩丝攒花结长穗"、"起草八团排穗"、"锦边弹墨"、"累丝嵌宝"、"朝阳五凤挂珠"、"赤金盘螭璎珞"、"双衡比目"、"二花捻珠"、"松花撒花"、"攒珠"、"洋绉银鼠"、"宫制堆纱"、"立蟒白狐腋"、"簪缨银翅"、"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碧玉红"、"金蟒狐腋"、"排穗"、"细折"、"麝香珠"、
所谓服饰,是服和饰的合称。《红楼梦》中非常重视饰物的运用,书中写到的饰品有"璎珞图"、"宫绦"、"钗"、"佩"、"金冠"、"抹额"、"箭袖"、"排穗"、"坠角"、"凤冠"、"昭君套"、"勒子"、"荷包"、"金魁星"、"念珠"、"朝珠"、"靴掖"、"扇囊"、"香袋儿"、"戒指"、"吉祥如意"、"耳坠子"、"麒麟"、"汗巾"、"鲛帕"、"一炷香"、"朝天凳"、"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手巾"、"包头"、"如意绦"、"观音兜"、"虾须镯"、"联垂"、"珊瑚"、"猫儿眼"、"祖母绿"、"一丈青"、"碧玉佩"、"慵妆髻"、"玉塞子"、"汉玉九龙佩"、"抹胸"、"脂玉圈带"、"妙常髻"、"尾念珠"……真是如古人所云:"一首之饰,盈千金之价;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这些饰物中有许多种类,不要说在18世纪时是罕见之物,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除了亿万富翁以外,绝大多数人还是要到"珠宝商店"里才能见识见识而已。
《红楼梦》服装中的款式,四季分明,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一应俱全。就连雨雪天用的斗笠、蓑衣、沙棠屐、雪帽,都一一写到。从款式上来说,有"窄裉袄"、"银鼠褂"、"洋绉裙"、"背心"、"水朝靴"、"大袄"、"花绫裤"、"霞帔"、"披风"、"皮裙"、"棉裙"、"斗篷"、"对衿褂"、"蟒袍"、"王帽"、"
《红楼梦》中不仅有服饰细致的静态描写,更有传神的"动态表演",反映了不同人物、不同场合、不同季节的不同穿戴。比如,贾宝玉的礼服着装:"头上戴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涤,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而王熙凤穿着褂服的形象是:"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红楼梦》展现中华服饰文明成果是全方位的,以上五点则是择其要者。此外,《红楼梦》在色彩运用、化妆等方面也有非常丰富的体现。
《红楼梦》中有名的"晴雯病补雀金裘"的故事,这件雀金裘"后襟上烧了一块","有指顶大的烧眼"。书中写道,让婆子们拿出让织补匠织补,可是"不但能干织补匠人,就连裁缝绣匠并作女工的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这一方面说明雀金裘确实名贵罕见,另一方面也告诉读者如同这样的服饰在制作工艺上的非常难度。市上的织补匠、裁缝匠都没见过也补不了,却由大观园内的一位俏丫鬟完成了,且是在病中补的。书中说,晴雯"细看了一会"就说出"这是孔雀金线织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得过去"。书中描写道:"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再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变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
这雀金裘应该是《红楼梦》中最有名的一件衣服,这是老太太送给宝玉的,是典型的舶来品,珍贵异常,一共也就得了两件这样的稀世珍宝,一件是野鸭子毛织成的,送给了薛宝琴,另一件就是雀金裘,送给了宝玉的。那么这件雀金裘究竟是何方神物呢?
“雀金裘”的不凡之处,在于它的衣料是在于它的衣料是“雀金呢”,是“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有趣的是,作者曹雪芹为强调“雀金呢”的珍稀,有意将之描写为“哦啰斯”(俄罗斯)的产品。这种描写虽然突出了贾府“白玉为堂金作马”的奢豪气势,却不符合历史事实。用这种工艺织成的高档织物当然也不叫“呢”,“呢”是一个西方语言词汇的音译,曹雪芹借用这个外来词,无非是赋予雀金裘一种浪漫的异域情调而已。
但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用孔雀毛或者动物毛编织早有存在,在清初叶梦珠的《阅世编》里,有这样一段话:"今有孔雀毛织入缎内,名曰毛锦,花更华丽,每匹不过十二尺,值银五十余两。"研究人员更是确定,明朝是有孔雀羽毛织进丝线的工艺,只是后来失传了。
八世纪的唐代大诗人王维在诗中如此描写当时天子接受外国使臣朝拜的情景: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清晨来临,负责掌管皇帝服饰的宫中女官“尚衣”向唐玄宗献上新制的“翠云裘”。自从唐太宗以来,唐朝皇帝就被四方远近尊奉为“天可汗”,逢到盛大朝仪,云集长安的王公、部落酋长、使节一起入宫参拜,非常壮观。随着一道道宫门依次打开,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列队走上层层丹墀,身着翠裘、头戴冕旒的“天可汗”高坐在大殿龙座上的端严身影,在香炉缕缕升起的芬烟缭绕中,一定给四方诸国的国使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吧。
由"翠云裘"一词来推测,诗中所写的这件唐代天子的龙袍应该是用翠鸟的羽毛捻线织成。想一想吧,在公元8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人尚全然不了解丝绸的秘密,在中国,人们已经熟练地把鸟羽的细绒捻成线,与丝线一起织成华贵衣料了,多么令人惊叹的神奇啊!想当年,唐玄宗的堂姐妹安乐公主曾经让尚方监"合百鸟毛"织成两件长裙,这两件百鸟羽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大约是利用了雉鸡等禽类羽毛能够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幻不同色彩的原理。
据史书记载,由安乐公主开了这种制作"毛裙"的风气,整个上层社会立刻风起效尤,结果造成了一场生态灾难。为了获得做鸟羽线的材料,长江、岭南的彩禽几乎被捕杀殆尽。到了唐玄宗登基之后,为了遏制奢靡之风,由朝廷正式下令禁止社会各阶层随意穿着这一类织鸟羽线的服装,采捕彩禽制作色线的风气才渐渐平息。不过,任何朝廷法令都抵挡不了人们的虚荣心,这种特殊的面料一直受到富贵阶层的追捧,自唐至清日益炽盛。
宋时,泾州一地的鸟羽线纺织技术是如此普及,即使小孩子也都能够把绒毛捻成线,织出带方胜花的彩锦。当地所产的这种织毛锦非常之轻,一匹锦的重量只有十五六两,异常昂贵。翠鸟毛呈现为微闪光泽的鲜蓝色,在各种鸟羽中颜色最为亮丽,因此成为这种工艺中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宋代广西出产的一种翡翠鸟,背毛上的翠色细绒便被用于捻线织做衣料,成为那个时代富贵阶层所热衷的奢侈品。
此外,其他如雉(野鸭)等彩禽的羽绒也都可以制作鸟羽线,君不见《红楼梦》中,贾母在赏给宝玉"雀金裘"的同时,还赏给宝琴一领"凫靥裘"斗篷,就是用"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实际上,在清代,人们还发展出一种"缂丝加毛"工艺,利用富有绒质感的鸟羽线织制出花木鸟兽题材的主题画面,镶嵌在屏风框内,陈设在居室中。孔雀羽线也是鸟羽线中的一种,因为光彩的效果特别强烈,因此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南史》中就已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末的南齐时代,有一位才华过人的皇太子-文惠太子,曾经巧动心思,指导工匠用孔雀毛织成一件翠毛裘,金翠炫丽,十分珍奇。不过,由于孔雀并非中原地区的原生禽鸟,在元代以前,孔雀羽属于很难得到的稀罕材料,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与之相关的纺织工艺并不流行,到了明清时代,这种以羽绒制作的碧线才得以大发异彩。大约也只有中国传统匠人的心灵手巧,才能发明出捻制孔雀羽线这样特殊的工艺啊。长长的羽尾上只有顶端的"珠毛"可以用于制线,要将这些短短的细绒毛旋绕着缠裹在一根长长的细蚕丝上,再用绿色丝线分节捆扎,以这种办法将孔雀羽绒固定在长丝上。如此在一根长丝上接连地缠绑好翠绒,就形成了"孔雀羽线"。同理,鸟羽线也是采下翠鸟的背绒、雉鸡的彩绒,缠捆在长丝上而成。更为神妙的是,这些孔雀羽线、鸟羽线是作为彩色纬线的一种,缠于织梭上,与其他缠有普通色线的织梭一起,以白丝线为经线,交相地织结成整幅的面料。因此,其成品就是一匹平滑的彩色丝绸,而在表面上这里那里地呈现出孔雀羽线或鸟羽线的局部花纹。
上世纪五十年代,明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土了大量帝后服饰,其中有一件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团龙妆花纱织成袍料",在纱地上织有团龙纹,龙的鳞、爪及头部均用孔雀羽线织成,至今色彩鲜艳;团龙纹中的龙、云、火珠等则用金线织出轮廊,极富有立体感,并且与孔雀羽线形成金翠交辉的效果。另一件万历皇帝"杏黄地云龙折技花孔雀羽妆花缎织成袍料",则用片金线和朱红、水粉、宝蓝、浅蓝、月白、明黄、墨绿、果绿、中绿、蓝绿、浅绛、白等十二种彩绒纬丝与孔雀线合织而成。男人可以身穿杏黄色的袍服,并有着如此丰富绚丽的色彩交错在衣面之上,在明朝人的观念里,灿烂鲜艳的色彩并不仅仅属于女性,而是属于高贵的人。宝玉的"雀金裘"正是这样一件织有孔雀羽线的斗篷。不过,按小说中的描写,此件斗篷竟然不是以孔雀羽线织出局部花纹,而是用这种特殊的碧线织成全幅的面料。也就是说,整件斗篷上都是孔雀羽线在暗闪翠泽。
其实,小说中的这种描写也不算夸张。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一件乾隆时代的御用蟒袍,是以缎子为面料,在其上,各色丝线只负责绣出云纹等陪衬性花纹,作为主题花纹的龙纹竟是用钉上无数小珍珠与红色小珊瑚珠的方法成形。此外,凡是没有花纹的缎面都绣满孔雀羽线,看上去,便成了一件以孔雀羽线为底色、其上凸现珍珠与珊瑚珠花纹的珠宝华服!清廷还将类似绣法的蟒袍赐给蒙古王公,可见,遍覆孔雀羽线的长袍,实在是清朝富有时代特色的一种高档男礼服。
至清代,织孔雀羽服饰在宫廷、贵族中更加流行,在故宫博物院、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处至今均保藏着清代生产的织有孔雀羽线的帝王服饰及衣料。在李少红执导的另一部电视剧《大明宫词》中,就曾出现“百鸟羽衣”。
新版红楼梦剧组真是有点以次充好地瞎扯蛋。孔雀羽线与金织捻在一起织出来的料子和鸟毛装能一样吗?而且我一直到现在才知道有人认为<大明宫词>里的”鸟毛装是百鸟羽衣啊。
据说此裙灵感来自安乐公主的百鸟裙,那么看看典籍中是如何记载这条著名的百鸟裙。<唐书,五行志>载:“安乐公主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旁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这里说安乐公主织了两条裙子,其中一条给了她的母亲韦皇后,这条裙子是用百鸟的羽毛织成的。但百鸟裙毕竟年代久远,雀金裘却是近在眼前的。既然红楼剧组也知道是孔雀羽毛不是雄孔雀尾毛,就不要大言不惭的说什么再现。一件衣服重达四公斤,这贾宝玉的身子怎么受得了。其实,现在做出来的那不是裘,准确讲是斗篷,雀金裘必须具备两样材料,一是孔雀毛线,一是金线,然后捻在一起,便是红楼梦中说的”孔雀金线”,所以可以想见这件服装的华美,按书中晴雯补裘的说法”也拿孔雀金线就象界线似的界密”,雀金裘其实便是中国从宋元开始流行发展的金锦工艺中的捻金,再看看新红楼剧组的说法是”由于羽毛上的“翎眼”要排列整齐对称,因此缝制时要一片半压着一片,同时还要兼顾前后左右,极为费时费力”,摆明了他这羽毛不是织的,是一片一片粘上去的.搞了半天,不是毛织物,还是鸟毛装.估计剧组也怕这鸟毛不牢靠,所以才”留出一定数量的孔雀羽毛以备补裘之需”。
看看真正的孔雀羽毛织成的效果,清代的实物,当然这个捻入金线,不过这种效果真的和粘了一身的鸟毛斗篷大不一样啊.这才是红楼剧组介绍的’由于羽绒短而硬,羽线在织入织物以后,不断岔出绒毛,在织物表面产生微凸的效果。孔雀羽线会隐隐闪动莹光,其碧丽辉煌的效果远非丝线所能比拟。”
因为这种编织方式的繁杂特殊,做出来的实物珍贵无比,这样的技艺震惊了世界。就在1985年日本筑波科技世博会,中国送展一件"孔雀羽织金妆花纱龙袍"复制品。这件龙袍的原型是1958年定陵出土的明代万历皇帝龙袍,后者出土后,不幸很快碳化褪色。定陵博物馆和全国的专家都非常痛心,复制文物成为当务之急,可寻遍全国,竟找不到会织造龙袍的工匠。1979年,这项复制工作落到南京云锦研究所的王道惠等人肩上。明万历帝龙袍,原本就出自江南织造。可是几百年过去,古老的织造工艺早已失传。要复制一件工艺失传的龙袍有多难,仅从整个工程耗费5年光景便可知一二。当然,这还不是困难的全部。龙袍出土后不幸碳化1979年,南京云锦研究所一行五人前往定陵,其中包括研究所所长以及当时的云锦技术研究骨干王道惠。他们的目的,一开始只是为了了解古代丝织品纹样。
在1958年定陵文物出土时,万历皇帝被挖掘出来时只有尸骨,他的肉身变成尸水淌在料子上,致使织锦龙袍有些变色,可是出土以后,龙袍却在短时间内碳化,过去的颜色已经几乎无法辨认,有些地方还有破损。王道惠还记得,当时的感觉"看了就心疼"。这件龙袍的全名是"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芾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长约17米,宽约70厘米。文物专家后来在这些龙袍料的腰封上,查到它出于江南织造。史料记载,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设官办织造机构,到了明清鼎盛时期,家家户户机杼声昼夜不停,秦淮河畔好不热闹。
始于东晋的南京云锦,因如天上的云霞而得名,在当时是宫廷的御用之物,这织金挑花的云锦,平民百姓也消费不起。定陵的这些龙袍料,正是南京云锦的巅峰之作。"没想到,去了以后,定陵提出来能不能由我们担当复制任务,这个项目就落在我们头上了。"于是,
1984年,历时5年复制的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终于下机。龙袍被送到北京参加鉴定会。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说,著名作家沈从文作为服饰专家评价道:"这件明皇朝袍料的选料、织纹、色彩、图案、织造技艺都同历史真品相同,堪称再现传世稀珍原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则说,读《红楼梦》,都知道有关孔雀羽能织成衣料,过去总觉得这是作家的夸张,没想到如今真的用孔雀羽织成了龙袍,才让人知道曹雪芹所说不假。作为当时复制工作的总负责人,王道惠说,龙袍所获得的认可,是她几十年从事云锦研究最大的成就。复制龙袍的工作繁琐而又困难。王道惠说,一开始很难摸到头绪,通过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研究,这件龙袍的织造技艺与现代的技术非常不同,它采用的是"纱地妆花"织造技法。当时询问了南京为数不多的老艺人,大家既没见过妆花纱,也没见过织纱的织机,这项技术到了这时,已经失传。为了研究它的织法,王道惠一个人驻在北京,一头扎进复制工作里,她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又查询各种记载有云锦的文献,甚至细数整件衣襟经纬向各由多少根丝线织成,希望以此准确还原明龙袍的样貌。那时候,定陵博物馆的保管员,常常看见她下了班还在工作,就叹道"怎么不知道休息"!与此同时,在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寻访民间的织机,找来一位新中国成立前在苏州、无锡一带装织机的老师傅,这位师傅提供的织机能织素纱,可是对妆花纱却无能为力。后来,云锦研究所又通过一年多的实验,终于制成了能织出大型整幅妆花纱的织机。
再现"宝玉雀金裘"除了织机和妆花纱的问题,龙袍的名贵,还在于使用了金线和孔雀羽。王道惠说,褪色的龙袍上,当时唯有17条龙依然色泽艳丽,还闪着五彩的光,这就是因为使用真金线和包裹了孔雀羽的丝线来做原料。南京郊区的龙潭,曾是明朝制作真金线的官营作坊。在当时,那里的南京金线金箔总厂是全国唯一还生产南京复原万历龙袍产真金线的地方。制作真金线,首先要把金块制成金箔。两人相对而坐,轮流举锤,经过3万多下的锤打,把一块厚重的黄金,变成轻如鸿毛的金箔,再把金箔粘在一种特殊纸张上,压紧抛光,最后裁成条,剥出金线,和蚕丝相互缠绕,捻搓成金丝线。这样的金线制作,需经历上百道工艺。有一组数据可以看出金线制作的要求:捶打1克18K黄金,能延展到1平方米。1万张金箔只有1毫米厚,人体的温度就能让它卷起来。那时候,云锦研究所搞龙袍复制,要打制真金线,金箔厂一位老工人就跟王道惠说,旧时有流传,龙袍的金线不用足金,而是用含有少量银的黄金打造,这样做出来的金线,色泽更亮。于是,云锦研究所就试验了老工人的方法,打制出来的真金线,果然比足金更鲜艳。至于孔雀羽,王道惠说,通过放大镜能看出,羽毛是粘在丝线上的,如果没有丝线,羽毛就没法织起来。于是她就通过定陵,找到北京动物园,收集孔雀掉下的羽毛。然后再把羽毛拿回南京,叫人一根根地用手工捻成线。整个龙袍复制所需孔雀丝线长达300多米。
这道捻孔雀羽的工艺,后来在写作研究报道时,竟被一些专家在古代文献里找到了依据。比如,《红楼梦》"晴雯补裘"一回里,讲到宝玉的一件"雀金裘"是"俄罗斯国用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历时5年终于下机1984年,历时5年复制的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终于下机。龙袍被送到北京参加鉴定会。当时新华社的报道说,著名作家沈从文作为服饰专家评价道:"这件明皇朝袍料的选料、织纹、色彩、图案、织造技艺都同历史真品相同,堪称再现传世稀珍原貌。"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位教授则说,读《红楼梦》,都知道有关孔雀羽能织成衣料,过去总觉得这是作家的夸张,没想到如今真的用孔雀羽织成了龙袍,才让人知道曹雪芹所说不假。作为当时复制工作的总负责人,王道惠说,龙袍所获得的认可,是她几十年从事云锦研究最大的成就。
龙袍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一件衣服,那是皇帝独有的,它的制作工艺自然是要比普通的衣裳金贵繁杂很多。但是红楼中贾宝玉那件华贵无比的雀金裘也没少让人花心思,首先是它的做工精致繁杂,它的工艺之复杂,《红楼梦》第五十二回,俏平儿情掩虾须镯,勇晴雯病补孔雀裘中就写得十分详细:“晴雯方才又闪了风,着了气,反觉更不好了。翻腾至掌灯,刚安静了些,只见宝玉回来,进门就?声顿脚。麝月忙问原故,宝玉道:"今儿老太太喜喜欢欢的给了这件褂子,谁知不防,后襟子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一面脱下来。麝月瞧时,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说:"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迸上了。这不值什么,赶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个能干织补匠人织上就是了。"说着,就用包袱包了,叫了一个嬷嬷送出去,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别给老太太、太太知道。"
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来,说:"不但织补匠,能干裁缝、绣匠并做女工的,问了,都不认的这是什么,都不敢揽。"麝月道:"这怎么好呢?明儿不穿也罢了。"宝玉道:"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过这个去呢。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道:"拿来我瞧瞧罢!没那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子又着急。"宝玉笑道:"这话倒说的是。"说着,便递给晴雯,又移过灯来,细瞧了一瞧。晴雯道:"这是孔雀金线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可混的过去。"麝月笑道:"孔雀线现成的,但这里除你,还有谁会界线?"晴雯道:"说不的我挣命罢了。"宝玉忙道:"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得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了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迸,实实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
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线。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这虽不很像,要补上也不很显。"宝玉道:"这就很好,那里又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晴雯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小一个竹弓钉绷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的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缝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地子来,后依本纹来回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宝玉在旁,一时又问:"吃些滚水不吃?"一时又命:"歇一歇。"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拿个枕头给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罢!再熬上半夜,明儿眼睛抠搂了,那恰怎么好?"玉见他着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毛来。麝月道:"这就很好,要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了瞧瞧,笑说:"真真一样了。"晴雯已嗽了几声,好容易补完了,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嗳哟"了一声,就身不由主睡下了。”悄悄,只是为了一个小小的破洞,就闹得人仰马翻,城里的那些巧手绣娘都问过了,也没人认识这衣裳的做工,最后还是亏了晴雯用界线的针法介密,这才算是面前补好了,看不出什么大的破绽。就那个一点点的小瑕疵就折腾了一个晚上,这件衣服的做工复杂,精巧,华贵可见一斑。
富贵如四大家族,穿衣打扮自然不是普通人家可比的,家里珍贵的衣裳也不止这一件。绫罗绸缎都只是寻常,就连云锦,缂丝之类在他们家竟也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姑娘们的衣裳更是华丽异常,在四十九回中就曾经略有描述。
《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可以说是“清初女式冬装流行款式发布会”。黛玉是“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众姐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戴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里面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褃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妆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麀皮小靴……”
“鹤氅”是《红楼梦》中最为常见的服饰之一,本为“神仙道士衣”,在这里已成为清初上层社会冬季“流行时装”,就是斗篷、披风之类的御寒长外衣。“鹤氅”二字,见于古代典籍。《晋书·谢万传》云:“著白纶巾,鹤氅裘。”《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五代史·卢程传》云:“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又据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以鸷毛为衣,谓之鹤氅者,美其名耳。”可知鹤氅是一种以鸟毛为原料的毛织物,故名。明刘若愚《明宫史》水集“氅衣”条云:“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之曰氅也。彩、素不拘。”大概样子像道袍,而不缝袖,所以披在身上像一只鹤。这种服装在明代宫中已有,勋臣贵族之家也纷纷效仿。清曹庭栋《养生随笔》卷三“衣”类云:“式如被幅,无两袖,而总折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坐亦可披以御寒。《世说》王恭披鹤氅行雪中,今制盖本此,故又名氅衣,办皮者为当。”
“羽纱”属毛织物,也称“羽毛纱”,疏细者称羽纱,厚密者称羽缎,制成衣服可防雨雪,出自荷兰、泰国,为外国贡品。清王士祯《皇华纪闻》中有记载:“西洋有羽缎、羽纱,以鸟羽毛织成,每一匹价至六七十金,着雨不湿”。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又说:“羽纱、羽缎,出海外荷兰、暹罗诸国。康熙初入贡止一二匹。今闽广多有之,盖缉百鸟鹬毛织成。” 据《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零三有关外国朝贡的记载,康熙二十五年,荷兰国的贡物中有“羽缎”、“羽缎”。雍正三年,西洋伊达里亚国教化王伯纳第多贡物中有“大红羽缎”。雍正五年,西洋傅尔都噶尔国王若望贡物中有“大红羽缎”。这都证明羽缎、羽纱是舶来品,在当时是十分稀贵之物。
至于“白狐狸里”,“讲究的用狐狸腋窝部分的皮毛,皮质轻软,毛色纯白,又称狐白。”:《史记·孟尝君列传》云:“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足见,白狐皮历来是名贵的皮裘。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也说:“凡狐貉亦产燕、齐、辽、汴诸道。纯白狐腋裘价与貂相仿。黄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御寒温体功用次于貂。”“洋线番羓丝”,是一种丝线和毛线混合的织物,也是一种“舶来品”。宝钗的这件“鹤氅”,应该是“指雪青色(也即是藕合色)方胜纹地加团花或折枝花的外来毛绒披风,当时这类材料有倭绒、倭罗绸、剪绒……等等。”
所谓“大红猩猩毡斗篷”,“即是用鲜艳的红色毛料制作的斗篷,因古谓猩猩血可作红颜料,所以后将艳红色称为‘猩红’而红毛料常被称为大红猩猩毡,毡作平面薄呢解。”
“褂子”,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满族人对外衣的称谓,进而引申为清代服饰名称。“褂子虽说在明代也有,但明方以智《通雅·衣服》中即说是‘今吴人谓之衫,北人谓之褂。’徐珂《清稗类钞·服饰》记载:‘褂,外衣也。礼服之加于袍外者,谓之外褂,男女皆同此名称,唯制式不同耳。’赵振民《中国衣冠中之满服成分》索性认为:‘中国古无“褂”字,……盖满制也。’”湘云所穿的“里外发烧大褂子”,就是里外都用皮毛作成的衣服。
所谓“昭君套”,也称“昭君卧兔”,是“用貂皮或其他细毛皮作成的帽兜,在额间耸聚如鹬冠,是女风帽一类。明末清初妇女冬装喜用到。”2为明清妇女常佩带的一种御寒额饰。樊彬《燕都杂咏》诗注云:“冬月闺中以貂皮覆额,名‘昭君套’。”这个“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昭君套”,是“指嫩黄色织金缎子挖成云头如意折边里子的大红毛呢面的女帽兜”。《红楼梦》中另一件十分“惹眼”的“昭君套”是第六回王熙凤“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昭君套作为妇女额饰不分年龄老少。至于这名字的由来,“当于王昭君出塞有关”。
除了那有名的“昭君套”,第六回中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也颇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回中王熙凤的打扮是“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这洋绉又是一件舶来品,是表面呈绉缩状的纺织物。“洋绉和后来之湖绉材料相近,多本色花。这里‘撒花’也可指丝绸上本色花。也可指在洋绉上另用铺绒法绣的散朵花。”
《红楼梦》里的“裙子”特别多,上面提到了凤姐儿的“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翡翠撒花洋绉裙”,袭人有“葱绿盘金彩绣绵裙”、“白绫细折儿裙子”,香菱有“石榴裙”……花样质地各不相同。从上面所举可以看出,清初女装裙子的选材各异、种类繁多。“按季节来说:有单裙、绵裙,进而还可以有皮裙……自然也该有夹裙。按折儿来说,有细折,自然也可以有粗折、宽折、大折或无折。按颜色来分,有葱绿、有白、有翡翠、有水红、有石榴红。按花纹来分有盘金彩绣、有撒花(即散花、碎花),自然也可以无花。按用料有妆缎、绫、洋绉、绸等等,自然也有布裙。”
清初上层妇女家常装束中,多是“明式领扣,……穿长比甲,裙作百摺,如明清之际南方常见流行样式……”在明清之际,还流行一种“月华裙”,为一种浅色画裙,裙幅共十幅(最初为六幅,所谓“裙拖六幅湘江水”),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如月华,因此得名。清代月华裙,在一裥之中,五色俱备,好似皎洁的月亮呈现晕耀光华。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裙装“作法是以绸缎裁剪成条状,每条绣以花卉纹样,两边以金线镶滚,走起路来,彩条飘舞,金线闪烁,颇似凤尾,称‘凤尾裙’。”
由于从明到清男装改变十分显著,且曹雪芹在创作时对社会政治的有意回避,因此,我们很难从《红楼梦》中看出太多的清初男装的样式,但是小说中也并非完全不留痕迹。如第十九回,宝玉的装扮:“大红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活脱的清代标准官服一袍一褂的瘦袖袍和貂褂。“所谓箭袖,实际上就是马蹄袖。它袖身窄小,袖端头为斜面,袖口面较长,可覆手,弧形,以便保暖,同时还不影响射箭动作。清代宫廷因极力主张不废除骑射,因此将箭袖用于礼服。”
清代男子服装主要有袍服、褂、袄、衫、裤等。袍褂是最主要的礼服。其中有一种行褂,长不过腰,袖仅掩肘,短衣短袖便于骑马,所以叫“马褂”。马褂的形制为对襟、大襟和缺襟(琵琶襟)之别。对襟马褂多当礼服。大襟马褂多当作常服,一般穿袍服外面。缺襟(琵琶襟)马褂多作为行装。马褂多为短袖,袖子宽大平直。颜色除黄色外,一般多一天青色或元青色作为礼服。其它深红、浅绿、酱紫、深蓝、深灰等都可作常服。
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服饰文化的嬗变也是民族文化传播、传承的重要表现。其所承载的民俗,是稳固的,是具有极强穿透力的,它往往可以穿越时空的阻隔,跨越人为的障碍。尽管曹雪芹极力想要借那一块不知何年何月的石头,来隐藏真实的时空背景,然而书中种种的服饰描写,依然清晰的呈现出清代服饰的特色。从《红楼梦》中的服饰形象上,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中国服饰艺术难以掩盖的美,以及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服饰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最扎实而厚重的再现,同时又是最浪漫而诗意的抒写。服饰文化,永远在文明的舞台上,闪耀着其璀璨的光芒!
RELATED RECOMMENDATION
相关推荐